 那天下午,我經歷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。
那天下午,我經歷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。
那是我第一次聽Spendor Classic 100喇叭;也是我第一次聽Norma Audio的擴大機。那天是我第一次去試聽;也是我第一次與這么多音響界的前輩一起試聽,不是交誼休閒,我是來工作的,甚至,其中還有國外原廠的老板。這次試聽,也是我第一次在經銷商遇到原廠老板親自調整喇叭后再讓我試聽的。太多新鮮的經驗,都在那一天下午發生。
我與上瑞張老師有約,要跟Norma Audio的老板Enrico Rossi見面。那天下午,也是編輯部安排我去統領音響試聽Spendor Classic 100的時間。訪談的地點就約在統領附近的咖啡廳,那間咖啡聽從外面看,怎么都不覺得會有好咖啡,結果,一試,還不錯。一個忙碌的下午,就該這樣以一杯好喝的咖啡開始。
我們聊了一個多小時,同時也在等待駱老板準備好。駱老板可不是偷懶,搞到別人要來聽了才準備器材。是因為那天張老師特別指示,希望這次讓Spendor Classic 100這對新推出的喇叭,能搭配一臺剛引進的擴大機,他對喇叭有信心,一定唱得好,也對這擴大機有信心,一定推得好。
這擴大機,就是Norma Audio的旗艦綜擴IPA-140。可是,全臺就這一臺啊!音響展后,這臺就被臺南經銷商帶回去了,張老師為了這篇報導,特地商請經銷商送上來,所以,要等。
訪談結束,我們才走個半分鐘,就到了統領。我第一次到統領,這才發現駱老板真不簡單。他賣出全球第一對Elac Concentro喇叭的事,名震江湖。可是,沒去過還真不知道,統領的試聽室竟然長這樣。

人定勝天,認真擺位克服空間不利條件
長怎樣呢?首先,這里很小,大概只有4坪大,坐在其中,我登時覺得,我有我家客廳可以聽音響,真是幸福。再者,這里不規則,不是一個標準的矩形空間,而是一個將近正方形的梯型空間。
正方型就夠要人命的了,何況左右還不對稱,連壁材也不對稱,這要怎么玩呢?駱老板憑他多年的經驗調音,我在試聽了幾曲后,竊聲跟駱老板表達佩服之意,因為我覺得這里的駐波沒有我想像中的嚴重,而且不會吵。
統領竟然能憑這樣絕對不理想的空間,賣掉Elac Concentro,駱老板真是不簡單。這也表示,您府上的音響需求,駱老板一定能滿足您,再怎樣疑難雜癥都沒問題。
外貌30年來幾乎不變,內在已然悉數革新

我知道您在想什么。我沒忘記這篇主角是誰。這次試聽的是Spendor Classic 100書架喇叭,與其說是書架,稱之為「需要腳架」(stand mount)的喇叭更為適合。
單是高度就有70公分,僅需墊高30公分左右,就達到落地喇叭的高度。3單體3音、低音反射式設計,而且,誠如其名,真是一派經典。事實上,它就是經典。打從1989年Spendor推出S100之后,接著在94年推出SP100的改款,繼之以SP100R2,而,Classic 100則是2017年才推出的最新版本。
單看照片,實在看不出Spendor Classic 100的魅力。實地見到喇叭,才深感這間老字號工廠,果然不愧是喇叭專家。即便看起來仍是40年前產品的樣貌,但骨子里,全不一樣了。這個Classic 100是去年才推出的新改款,單體材料都不同。Classic系列的改款是從2015年推出旗艦喇叭SP200開始,事隔兩年才正式將整個系列的新款喇叭一一補齊。

采用全新單體,提升整體表現
Classic 100的單體排列順序,由上而下是中音、高音、低音。我們還是從高音開始講起。高音單體採用一顆22mm的高音,材質則是一種人造的塑料纖維,質量更輕,有助于高頻延伸。
高音上方是一只180mm的聚合物振膜中音,這個被稱為EP77的聚合物振膜,是原廠最新開發出來的振膜,同樣可見于D系列喇叭。聚合物振膜向以質量輕、內阻高著稱,因此反應速度快,聲音清晰而有透明感,并且極少帶有材質本身的音染。
中音單體的中央,還有一個子彈型的相位錐,有助于打散錐盆底部的聲波諧振,以利聲音清晰還原。至于下方的低音單體,則是一只300mm的大口徑低音,振膜採用複合Kevlar纖維製成。材料本身硬度夠高,不易發生形變,同樣具備低失真的特性。
箱體外觀雖然維持40年前錄音室鑑聽喇叭的古樸樣貌,但箱體材料則不一樣了。Classic 100使用MDF板,并且各部位的板材厚度不一,針對各面的振動控制而做設定。內部則盡可能減少吸音材使用,好使聲音更透明自然。
高音上方是一只180mm的聚合物振膜中音,這個被稱為EP77的聚合物振膜,是原廠最新開發出來的振膜,同樣可見于D系列喇叭。聚合物振膜向以質量輕、內阻高著稱,因此反應速度快,聲音清晰而有透明感,并且極少帶有材質本身的音染。
箱體外觀雖然維持40年前錄音室鑑聽喇叭的古樸樣貌,但箱體材料則不一樣了。Classic 100使用MDF板,并且各部位的板材厚度不一,針對各面的振動控制而做設定。內部則盡可能減少吸音材使用,好使聲音更透明自然。
面網採用磁吸設計,可輕松移除面網以聽見更優質的表現。低音反射孔位于喇叭正面,開口的擴張弧度設計,有助于導出氣流。背后的喇叭端子都是鍍金品,一共預備了三組,讓您最多可玩tri-wire、tri-amp。不想麻煩也沒關系,用跳線連起來,一樣很好聽。這次試聽就是這樣。


 Norma Audio老板親自調整擺位
Norma Audio老板親自調整擺位
準備好試聽了嗎?我是準備好了,但還有人有意見。
這次負責推Classic 100的是Norma IPA-140綜合擴大機,Norma老板Rossi在此,當然要調到最佳狀態才行。這里雖然不是他的地盤,不若駱先生那樣熟悉此地的聲學條件,Rossi仍提出請求—他要調整喇叭。
他從背包里翻出一張燒錄光碟,CD盒上夾了一張曲目單,里頭都是挑選過的樂段,是他拿來測試音響的法寶。他請代理商協助,聽他指揮。內傾、拉開、朝外一點、往內靠一點...,他一邊聽,一邊指揮。只見他閉上眼睛,雙唇輕闔,神情專注凝重,彷彿在進行一場神圣的儀式。

這期間,他都聽了什么?我沒過問他試聽的每一軌出處,但有印象的,也是他反覆聆聽的,則有吉他、人聲和鼓。我大概猜到得他想聽得什么,他要抓出高頻的甜潤與光澤、中頻的解析與厚度,再加上低頻的層次和重量。
此外,他注意到統領試聽室狹窄的空間,擺滿了器材,若讓右聲道朝前發聲,其實會直接打到右側擺滿器材的器材柜。況且,右側離墻近,左側較遠。最終他採用較大角度的toe-in,讓Classic 100直接正對聆聽位置。這種擺法是在小空間里,為避免側墻過多反射音的標準作法。
Rossi示意已經調好了,要我坐過去。他欠身往沙發邊靠去,我在CD匣里挑了一張CD。我有意測試Rossi的調整功力。他在1987到1991年期間,也待過義大利的音響雜志,當時他負責在實驗室里針對送評器材做儀測并分析電路,是媒體前輩,后來又當音響公司老板,是業界前輩。我想知道他在短短10分鐘內怎么在一個陌生的環境里調好喇叭。我也用類似的音樂來驗證最快。

黃金交叉點上的魅力人聲
 這第一張CD是法國女高音Patricia Petibon演唱西班牙歌曲的專輯「Melancolia」。錄音當中有女高音的演唱,有一個古樂編制的室內樂團,并且配有吉他以及一些民俗樂器。音樂一放,Petibon的聲音凝聚,定位在中央偏做一點的位置,而且音像立體。她歌唱當中不時改換音調,抑揚頓挫。
這第一張CD是法國女高音Patricia Petibon演唱西班牙歌曲的專輯「Melancolia」。錄音當中有女高音的演唱,有一個古樂編制的室內樂團,并且配有吉他以及一些民俗樂器。音樂一放,Petibon的聲音凝聚,定位在中央偏做一點的位置,而且音像立體。她歌唱當中不時改換音調,抑揚頓挫。
這樣唱,不容易,這樣的錄音,要表現,也不容易。Classic 100這時把Petibon這些變化多端的唱腔表現得可精彩。有形體,卻不濃重,Petibon是輕女高音,能唱點花腔。這些歌曲需要的,正是Petibon的那種輕盈靈巧的聲腔,若濃重了,聲音就沒有那種活潑性了。Classic 100此時表現出的人聲實在有魅力。
我也注意到樂團的部分,雖然樂團規模不大,但弦樂依舊迷人,特別是當大提琴和低音大提琴頓下去時,Classic 100的豐沛低音讓我著實驚訝,怎地這么豐厚,怎地這樣有重量。下盤既穩,音樂走起來也就更穩,Petibon一唱,浮凸立體宛若雕像般活生的形象,搭配起樂團的跌宕起伏,那正是音樂動人之處。
而且,以上的聽感都是在我身體往前靠,像是Rossi調音時的坐姿那樣聽到的,若我偷個懶,往椅背靠下,聲音就沒那樣活生立體,聲音的光彩也要登時銳減。這調音,不是皇帝位,根本是黃金交叉點。
完了嗎?還沒。這張專輯還特別找了吉他演奏家Daniel Manzanas助陣。我在許多系統,也在不同的地方聽過這張專輯,我非常清楚這吉他可以有怎樣鮮活而圓潤的質地表現。
在這里,我并不認為是最好的經驗,因為受限于空間,加上較多的toe-in角度,發聲體的分離度沒辦法拉開,弱在層次,卻勝在那琴音的真實感。這里的吉他只是伴奏,只是點綴,可是,我聽到吉他撥奏錚錚鏦鏦,質地是緻密的,顆粒是圓滑的,色彩是清潤的,光澤是暖和的,在一片弦樂聲中穿透將來。
我放的吉他,不同于Rossi,這是古典,他是鋼弦;我放的人聲,也不同于Rossi,這是聲樂女聲,他是民謠男唱;我放的低音,依舊不同于Rossi,這是低音提琴,他是震聲大鼓。然而,他的滿足,我一下子都瞭然于胸了。

聽見細微聲腔變化,宛若親臨現場

再聽Maria Jaell的聲樂作品,依舊是女高音,伴奏卻換成鋼琴。只聽第一軌和第二軌。第一曲是一片溫柔抒情,唱得溫柔,琴也溫柔。但溫柔之間,就有許多細節,一慢,一輕,很多細微的聲腔變化運轉,就成了觀戰重點。我聽到的人聲好清楚,就像剛剛聽Petibon唱歌一樣,那是一個人,一個面容,吟哦一首詩。
琴音帶有一種飽滿的顆粒質地,在我的經驗里,這里顆粒的渾圓感特別鮮明,鮮甜之馀還有豐富水分。這是Classic 100的功勞?還是Norma IPA-140好聽?我聽的欣喜,轉頭問一旁的張老師,張老師答得妙:「都好聽。」哈哈,是啊,但我不覺這是老王賣瓜。
在試聽之前與Rossi訪談之時,Rossi就跟我說一個觀念:「喇叭決定了音樂重播時的音色平衡,但其他諸如音質、動態、音場等,都是擴大機決定的。」所以,他非常注重Norma擴大機的「質」(quality),沒有好的質,喇叭也出不了好聲音。料想這質,Norma貢獻良多。
第二曲「貓頭鷹」的動態鮮明,有極弱的演唱和演奏,又有極強的樂段,單是開頭的鋼琴就夠震撼了。聽這鋼琴的厚度和重量,推估跟toe-in角度有關,若少些內傾,恐怕琴聲會薄一點,但弦振細節以及共鳴音色會更顯明。這里的鋼琴漂亮過關,震撼到心底去了。

活生、具體、沖擊力

爵士樂最能展現系統的活生感。放上鼓手Bertrand Renaudin領軍錄製的La traversee du jour專輯。我發現這個系統的有著敏捷的反應速度,聲音完全沒有拖遲感,聲音細節清楚明確,且每個細節都有畫面,打擊樂不僅活生,而且見得此系統的動態表現驚人。
第一軌音樂一下,打擊樂渾圓飽滿的顆粒登時迸現,鋼弦吉他刷下可以見得力道,聲音是有沖擊感的,長笛吹奏的聲音帶有圓潤質地以及氣音細節。第二軌的鈴鼓敲打起來真是活生,手觸鼓面發出乾而短促的聲音,但敲擊的剎那,鼓邊的金屬片撞擊聲清脆而且具體。
第三軌的電吉他嘶吼聽起來有沖擊感卻不刺激,這可是大角度toe-in的擺位,單體幾乎正對聆聽位置,但是系統本身的失真低,噪感就少,再加上空間的藕合,才造就了這辛辣卻不噪熱的吉他味。
腳踩大鼓真是兇悍,一般體型的書架喇叭還真難聽得那飽滿鼓聲,但Classic 100不是普通的書架喇叭,或者說,它不是一般意義的書架喇叭,那個300mm的低音單體不是蓋的。厚重扎實而且深富力道的鼓聲,在我想像里應當發自體積更大的喇叭,才有這等能量。Classic 100在有限的體積內,真是發揮了最大的重播效能。
打擊樂最熱鬧的當是第六軌和第十二軌到十五軌的音樂,鼓聲俐落且速度飛快,深沉處則重量、力量兼有。因為稍早才與Rossi訪談,他的話一直映在心里。Rossi說Norma的擴大機的特點就包括了大電流輸出和高阻尼因數、高迴轉率,這讓擴大機對喇叭的控制能精確而得心應手。是這樣嗎?我聽到的精彩聲音,應該就是Rossi此言的證明。
我轉頭問一下駱老板,經過重新擺位后,聲音跟他事先的調教有什么差別?「低頻駐波比較少了。」我相信。這播放的幾軌鼓聲深沉重擊下,都展現了乾淨的低頻,在第九軌里的電貝斯低鳴,如果低頻駐波嚴重,會讓聲音聽來糊糊的,缺少顆粒感和明確性。這時我聽到的可清楚了。
而且在電貝斯和打擊樂的襯底下,透出的次中音薩克斯風圓潤溫厚,帶著空氣嘶嘶的摩擦感,真是好聽。誰說樣子老派就是老聲,誰說英國喇叭就是溫吞?
一曲芬蘭頌,眾人都被帶到音樂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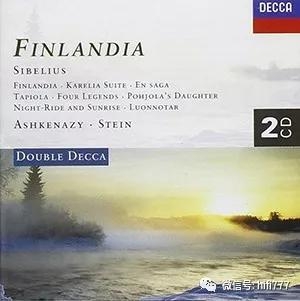
雖然空間小,喇叭距離拉得也不甚開,誰說這樣就不能聽大編制的管弦樂了?放上Ashkenazy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西貝流士交響詩芬蘭頌,就可見得這個系統,能夠多威猛;即或Spendor Classic 100看起來是這樣道貌岸然,但唱起芬蘭頌可熱了。
樂曲開頭,伸縮號搭配法國號吹出深遠綿長的樂句,低音號以低沉粗獷的腔調幫襯著,低音提琴以長音柔化了銅管的金屬況味,此時,加入的小號則把旭日東升的輝煌感帶了出來。短短的開頭,若把這些樂音都聽明白了,把這些音樂中交融的色彩都看清楚了,這曲子就精彩了。
背后滾來的定音鼓,顆顆飽滿,聲聲確實。弦樂不僅有密度,還有高度的張力,帶著柔韌的織物質感隨著旋律翻騰飄盪,是云亦是海,是風也是浪。點綴的三角鐵,穿透層層霧障而出,清脆亮麗而且飄逸飛揚,畫龍還需點睛,果不其然。
我越聽越入神,越聽里頭越是激昂;但又豈止我呢,一伙人早就都放下手機,一起進入西貝流士對祖國的歌詠深情里了。早些我放的幾張CD,Rossi每一張都借來看,他非常享受那音樂。
這芬蘭頌一放完,我們幾個不禁討論起錄音版本來了。聽音樂本當如此,音響永遠是為音樂服務的,如果音響把我們帶到音樂里,那音響就高竿了,如果只能讓我們停留在對聲音的感知,那就還不是Hi End。
細致的弦樂,有機的聲音

我再放上Stanislaw Skrowaczewski指揮明尼蘇達管弦樂團的布魯克納第九號交響曲,這是Reference Recording的錄音,我不是沖著RR錄音放這片的,我是為了Skrowaczewski來著的,他是其中一位讓我認定是布魯克納專家的指揮。
第九號交響曲雖然不像芬蘭頌那樣激烈昂揚,也沒有火鳥或布蘭詩歌里那種突然乍現的大動態。可是,這曲子柔美之中可見許多交響音樂的精彩,系統越好,這曲子越能完整重現。
這當中最考驗音響的是動態幅度。雖然不是瞬間爆發的對比,卻多的是微小的騷動以及樂團張揚的齊鳴。至于RR錄音向來具有高度透明,可以見得非常清晰的音場和層次。
在Classic 100的演示下,這曲子真是美得無比。弦樂不僅有絲滑質感,還有絲綢光滑,Classic 100不過是軟半球高音,怎地高頻可以如此漂亮?那種纖細質感,又有密度和光澤,直逼高級絲帶高音才有的高音表現。
我不禁在筆記本上留下「弦樂細緻度,首度體驗」的備忘。撰文時,我一度考慮要不要把這段筆記寫出來,就怕讀者以為是吹捧,幾經思索,我還是寫下,因為這是我的真實經驗。
我覺得這是Classic 100對于細節重播的不妥協性能所致。它有非常豐富的資訊量,如此,才建構起這樣高組織性的聲音。我用這個詞來形容—「有機的」(organic),這聲音一點不造作,一點不人為,非常自然,卻又如此真實。如果不是常到音樂廳聆聽現場演出,就不會在聽見這布魯克納第九時,有這樣的感動。
單是聽到第一樂章尾奏的銅管三連音后堆疊起的音樂情緒,再以樂團齊奏達到頂點,情緒就要沸騰了。
就在此時,轉入第二樂章,弦樂以撥奏方式奏出詼諧曲的主題,這里,布魯克納再次運用三連音帶領音樂發展。這樂章里的動態起伏是巨大的,特別是弱奏時的細微纖柔,對比于管弦齊放后的萬鈞勢力,聽著聽著也不禁佩服起Norma IPA-140,Rossi說他重視的要素,確實在這里都聽見了—速度、動態、純淨、低噪、質感、活潑。我很喜歡那個透明到一望無際的音場,舞臺深度一覽無遺,當定音鼓擂動時,不僅有實體、實像,有力量、重量,還有距離樣貌。

 器材規格
器材規格
|